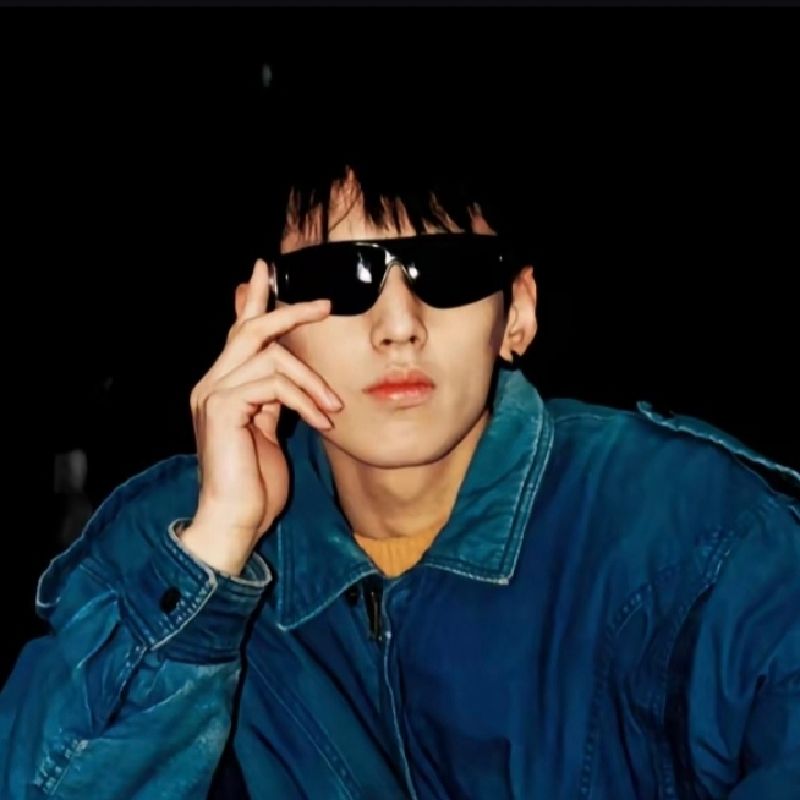以后想每天睡觉前发一张图片
 嘤鸣 遇见思想共鸣
嘤鸣 遇见思想共鸣 顾均临
- 今天我吃饭的时候,朋友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我不喜欢自我的人,我下意识的在想我是不是一个自我的人,然后说了一句我还挺想成为一个自我的人。 其实很多时刻的我自己看来,自我是一种对于自我内核的绝对自信,是不需要答案的践行者,而我一直以来这种时刻没有很多次,一面对选择就开始先从他人想起。 自我和自我意识不一样,不包括内省和犹豫,不需要时间和条件,不等同于自私和自负,更像是一种绝对的不需要在乎一切的内心平衡,当然,这是一种对自我理想化以及抛开其他条件的存在。 通常来讲,自我带给别人的更多的是不好的体验,在我看来,可能是自我的人更不容易产生自我意识,并且要面临把自己的内心世界高度隔绝的问题,我还没想明白。 就像我朋友接着说我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真的很好说话吗,我就在想,我是在营造一个我好说话的假象还是我真的很好说话,我喜欢别人说我好说话还是我不在意好不好说话。 答案是我确实是这样的人,并且在一般情况下我尽可能转变条件让自己好说话。 这种情况太明显了,有时候会下意识的观察别人的反应。有一次1把水洒在了2的电脑上,1在道歉并且补救,2第一时间没有言语,但是之后强调了电脑的贵重。 这里无法和自我挂上钩,但很明显1不是自我的对立面,即他人。我没有想到合适的词来形容。 同样的条件下,真实发生,1打翻水杯,浸投了3的笔记,一摞手写并且包含笔记的A4纸,不论贵重的问题,而是晾干之后的变形和字迹花乱。毕竟没有电脑外壳。 3同样第一时间无言语,一层一层的将上面浸水的纸张先剥离,然后讲没事,马上会干。 当时我真的在想小事,无论怎样都会干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种自己体谅他人的开心。 很小的事情对吧。我在察言观色。尽可能的让心理条件发生改变。 我有时候同样也在想,一些话不要说,一些事不要做会不会好一点,好一点点也可以,我要是破除阻碍乘上过去的一趟列车会不会不一样。 但其实归根结底,我的自我并不能高度隔绝,我需要在自我世界中的发生的重点事件和可遇不可求的重点人物的推进下,不断产生新的自我意识,尽可能的修补空缺的部分。 所以说过去的自己会是一种牺牲品。过去的照片也是,这几张照片是去年拍的,一直躺在手机里,或许等到今天又翻出来,它们很开心。 过去是一个节点,会把气味,现象和记忆串联在一起,营造一种过去很美好的假象。我的自我意识现在就告诉我不要迷信过去。 我总是想自己是蠢笨的,他人或许稍微聪明些。 但其实有时候也不是。 事物发展和人物交错的某个瞬间我特别想到上帝视角去走一趟,告诉特定的人一切都是误会,莫错怪。事情并不简单,但是发展就是阴差阳错。 如果说一个人让我觉得很遗憾,或者说在回忆里显得有点“可恶”,我需要尽可能的黑化这个人物,来避免过度自省,我需要明确的知道我没有错,或者出现了问题,问题没有答案,我无法解决。 很多时候不用太上心,这样就不会很伤心。 我觉得目前的自己仍然处于一种自我意识打地基的状态,可能很多时刻的想法或者说领会有,但是不会上升,因为可能一上升到头脑风暴我就会很耗费时间。 说不定那时候就不想说这么多的话,自然而然的发几张照片。
- 加载中...